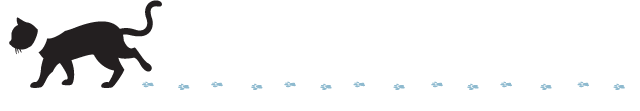延续奥尔传统的最后余脉
DEC
23
这份访谈从他的师承谈起,涉及面很广,既有他的“艺术个性观”、练琴要诀,也有他对作曲家的理解、对录音工业的反思,最珍贵的也许还有对同行名家的回忆。
务必听听看他的克罗采。
苏利文(Robert J· Sullivan) 采访
Nolix 编译
anonymous v兄 审校
刊载于2015年4月三联《爱乐》 文章来源于网络 ,
Sullivan: 您最骄傲的录音是哪几个?或者说,有没有最爱?
Rosand: 很难回答。不过总有几个令我重听时击节赞赏,而有些我听得不怎么舒服,因为记得清当时拉的一切细节,如多年前的门德尔松。那时的我还生着病,发着烧,只能坐着拉琴,那简直处于另外一个世界里。你今天听的话,会发觉简直快得吓人,正常的我不会那么做。
(编者注:确实是很吓人的速度……= =)
Sullivan: 终曲里简直是火箭的速度,其实很棒。
Rosand: 但即便听第一、第二乐章,我也不相信曲子能拉这么快。
Sullivan: 华彩段落拉得太漂亮了,何况是对于一个正在发烧的人。
Rosand: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我拉匈牙利舞曲的录音。当我今天重听的时候觉得挺有意思。另外,我对自己的无伴奏作品比如巴赫与伊萨伊很骄傲。我希望在1995年的春天之前录完巴赫的全部六首奏鸣曲,出于我个人的热望吧(译者注:此处应指指为小提琴和大键琴所作的六首奏鸣曲六首奏鸣曲,,BWV 1014-1019)。但我想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处理巴赫,一种更人性化的理解。你想,巴赫据说育有20来个孩子?所以他无疑是很有人情味的一个人,我想将其浪漫的一面在曲子里展现出来。

关于揉弦(或者不揉)
Sullivan: 您好像已经在亨德尔里展现出了这一点。显然它并不枯燥——既有揉弦,又有连奏,但音乐里的歌唱性如何表现出来,也是一个问题。
Rosand: 老实说,我并不想尝试赶上两三百年之前时的效果。这么做没有太大意义。这么说吧,对于不揉弦的、使用古乐器的做法我的确佩服,但这个时代里也有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和别人的看法不同。为了音乐的效果不变得轻佻,需要的只是在“文体”(stylistically)上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就够了,所以没有必要完全摒弃揉弦和滑音。
事实上,每一位作曲家都需要一种不同的揉弦方式。而微调揉弦则很可能是小提琴家通往成功的关键。你必须学着如何控制你的揉弦速度,并根据音乐性格决定揉弦幅度的宽窄。若揉弦过窄、过快,则很可能不太适合古典风格。而你操练揉弦的方法应是先尽可能地在一个乐句里保持平稳,避免在音符间或每一次换弓间冷不防地停顿或者变速。当手指有了稳定的动量时,不要停下,直到出现快速的行进章节。你应该试着取得一种古典的效果,而非过于夸张,因为那样容易腻味。同时还要记着,巴赫的作品尽可能少揉,而在赋格里则完全摒弃。
Sullivan: 我听过您所有的贝多芬奏鸣曲录音。

亚伦罗桑录制的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全集,我一直很想淘一张
Rosand: 其实,我是最早录制贝多芬所有写给小提琴和钢琴作品的演奏家,我的意思是,包括了“若你想起舞”主题变奏曲和一些非常早期的作品,如德国舞曲和回旋曲。所有录完之后,两个VOXBOX就装满了。我希望他们哪天重新发行一次。那时我三十多岁,还很年轻,是与第一任妻子弗里斯勒合作的。我们采用的奏法很忠实,对谱子上一切都受命奉行。况且之前,我们还读了两卷本的贝多芬书信集,感觉贝多芬仿佛已是我们很亲密的人了。

忠实于作曲家原意,比比想象里要难
Sullivan: 那个“春天”真是美妙。
Rosand: 我倒对克鲁采特别自豪。那时我们真年轻啊。以我看来,现在的“春天”都被拉得过慢了,一些小提琴家甚至完全不顾贝多芬亲手定下的节拍器速度记号。你要清楚一件事:梅尔泽尔,也就是节拍器的发明者曾送给了贝多芬一台最好的节拍器。可惜的是,我们常常会忽视他已经写入好多谱子里的节拍器速度,甚至会开玩笑说怎么能拉得这么快,节拍器不要爆表了吗?可是,真应该这么快!
Sullivan: 海菲茨“春天”的速度同样非常快。
Rosand: 他也许是最忠实原意的。贝多芬的原文是“allegro moderato”——中度的快板。顺便说一句,有时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竟然会耗费一个小时!我听过那样的现场时一时间还不敢相信。第一乐章是三十到三十五分钟,这么一来前后就有点不均衡了。事实上,贝多芬的错误在于当第三乐章写完之后,他的才思还远远没有用完。我记得好像是布里奇陶尔拉的首演是吧,真是可怜的家伙。好像他还为了取悦观众在乐章之间将琴颠倒过来演奏。可想而知,演出的反响真糟糕。
(罗桑说着哼出了独奏小提琴的前几个小节)您能否想象它在钢琴上的样子?没有谁敢真地去尝试这种速度。我记得曾看过一份很有趣的节目单,是索尔蒂爵士的。内容是第八交响曲,很正常,不过从头至尾竟然忠实地以贝多芬的节拍器速度演奏。那天的效果真是惊人,要知道花了索尔蒂五十年才找出贝多芬真正的所思所想,而它们才是应该注意的事情。

延续奥尔传统的最后余脉
Sullivan: 在您那张《小提琴家》专辑里,我最喜欢的录音是诺瓦切克的《无穷动》和克莱斯勒的《美丽的罗斯玛琳》。
Rosand: 您是否知道,当我开始拉克莱斯勒的时候,克莱斯勒已经很久没人拉了。事实上,逝世后人们几乎将他忘记了,也不怎么再版他的唱片,但是现在,每个人又都在拉他,这种情形有点像萨拉萨蒂。那个时期我大概出产了两三个录音。维塔利的恰空我用的是奥尔的版本,还有采用了克莱斯勒华彩与修订的《魔鬼的颤音》。而这些足以拿来作为音乐会开场的曲目,已经完全被当今的小提琴家忽视了。可是今天,小提琴家们多以巴托克的奏鸣曲或者贝多芬的“克鲁采”奏鸣曲开场,这一做法于我而言难以想象。不仅演奏者未能“热身”,观众的听觉也没能“热身”。
Sullivan: 我觉得您恐怕是奥尔传承中的最后一批人之一了。
Rosand: 这正是我为什么花大量时间去教学的原因。我觉得保持传统恐怕是我现在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在奥尔于上个世纪之交所开创的传统——米尔斯坦、海菲兹、津巴利斯特和赛德尔等人,不应该就这么走向终结。何况,柯蒂斯音乐学院是独一无二的。还记得那时皮亚蒂格尔斯每逢周六都会带我们去吃熏鲑鱼和面包圈,他总是喜欢与年轻人一起娱乐,并说一些有趣的故事。他是一个多么特别的艺术家和彬彬有礼的绅士!我随他学习室内乐,因此常常在他家参与演奏,我的早年受到了皮亚蒂格尔斯很大的影响。

皮亚蒂戈尔斯基,他录制的德沃夏克和圣桑大提琴协奏曲极为精彩
Rosand: 津巴利斯特除了教会我如何分句,如何用弓子呼吸,还懂得所有方法,包括“数数”的科学。他认为,没有一首曲子是以“1”开始的,因为第一音的作用仅仅是建立起曲子的调性。而真正的曲子实际上是从第二个音符开始的。仔细想想倒有道理!他打了个比方:“如果我们拉一首四拍子的曲子,打拍子其实不应该是1、2、3、4,1、2、3、4,我们又不是军乐队!”他说,正确的方法是,1,1、2、3,再来1,1、2、3,诸如此类。所以,就纯音乐的概念上理解,“1”其实是上一个乐句的结束。你可以想象,这样的理论对于我们影响有多大!
那时,绝妙的长笛演奏家金赛德也在柯蒂斯,还有难以置信的巴松管高手勋巴赫 、低音提琴演奏家托雷洛等等,小提琴有了不起的戈德伯格(Szymon Goldberg),钢琴系有格拉夫曼、莱昂·弗莱舍、利普金和弗朗克(Claude Frank)等等。那时的费城交响乐团顺理成章地处于鼎盛期。其实这就是规律——更好的音乐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今天也不例外。

Sullivan: 我一度期望自己拥有卓越的驾驭某一件乐器的能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听到那些早夭的天才——哈希德、卡佩尔、拉宾的故事时觉得命运非常不公的缘故。
Rosand: 拉宾真是一个悲剧,我听到消息时还不敢相信。
Sullivan: 他在丛书《我们的演奏之法》(The Way They Play)里和您在同一卷。照片里,他披着浴衣,一手端着咖啡,另一手拿着那把(原属库贝利克)的小提琴。瞧,就是这样的性格。
Rosand: 他后来有了一种畏惧症:不敢站到舞台的边缘去。他害怕自己可能跌落,于是开始坐着拉琴。
Sullivan: 他所拉的维尼亚夫斯基第一协奏曲真是我的最爱。对了,顺便问一句,津巴利斯特有没有让你练习那首颤音曲子——恩格尔的《海螺》?(译者注:Carl Engel 是法裔美国音乐理论家及钢琴家,此曲本写给人声和钢琴,是津巴利斯特作了改编。)
Rosand: 我很喜欢这首,也一再地以演奏它来纪念恩师,因为他大部分音乐会都会选择这首作为安可。

经久不衰呢。
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会拉琴 会教琴 会扯淡
什么都会一点 你想问点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