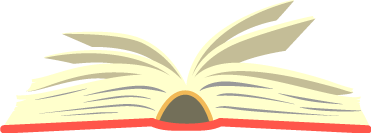
请点击上方“文学鉴赏与写作”免费订阅
让阅读成为习惯,让灵魂拥有温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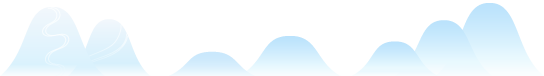
作者简介
![]()
李默涵,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学生,喜欢戏剧和桥牌。喜欢鲁迅先生的诗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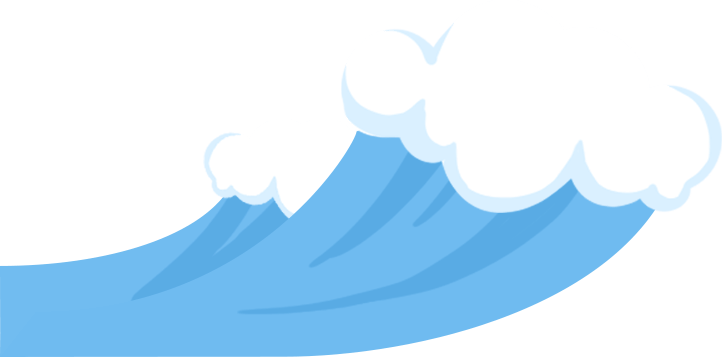
筒子楼上的小提琴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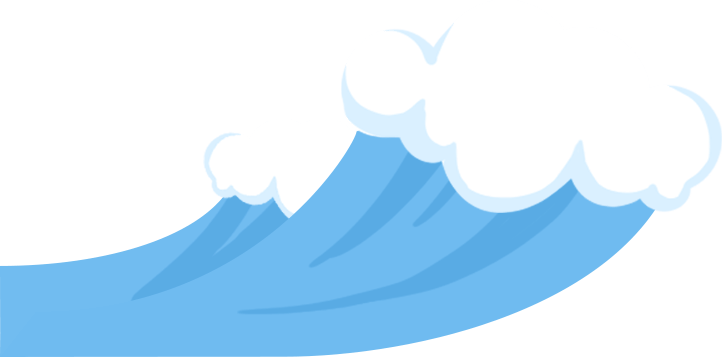
龙兄他妈是汉中人,讲一口不十分标准的四川普通话。她不留长发,中等个子,胯窄窄的,人瘦得干巴巴的。
像她这样的女人,大抵是有些脾气胆气的。早些时候得罪了部队大院的领导,她和丈夫只分到一间筒子楼的房子,住了十来年,院儿里就是不给她家换房子。院儿里不说,他妈也不提,该买菜买菜,该买肉买肉,到公用厨房做了饭,热气飘过一楼道,端回自家吃。
就这么过了十几年,筒子楼的年轻人搬走了一波又一波,龙兄他妈倒成了唯一住筒子楼的团职干部了——龙兄他妈就是这样的人,自己狠着绷着一根弦,旁人谁也不敢惹。
龙兄是跟我一院儿里长大的情同手足的发小儿,写全名显得生分,又想不起来他不粗鄙的外号,便依照我称呼名字中有龙字的同龄人的一贯做法,称他龙兄。
大概因为在开饭前常用勺子发射私藏的小珠子互射,我和龙兄常常被幼儿园阿姨叫到空出来的一张小桌子来,在她的监视下吃饭,这使得我与龙兄很早就有了一种患难与共的“狱友”情谊。
在上大班时,我还和龙兄秘密策划过逃离幼儿园,不过由于种种不可控因素,我们的计划最终并没有得到施行。
后来进了我们院儿共建小学(偏远的部队单位会和地方的小学共建,以解决子弟入学问题),没珠子给我们射着玩儿了。更不幸的是,我和龙兄没有分在一个班,聊不了了。我们每天也只能在早晚坐班车上下学时见见面(来去总共只有两个小时),龙兄还常常忙于吃早点、擦洒出来的牛奶、与押运我们的司机班的年轻战士斗智斗勇、吐槽他们班班主任或是补作业,剩下的时间根本不够我们聊的。大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大人们都开始露出他们原有的狰狞面目。
最明显的是,母亲们开始监督孩子们学琴练琴,由此,原本平静的院儿不知添了多少琴声和哭声。这风潮是从南边的院儿兴起来的,传到我们院儿时,那院儿的孩子每人都学了至少一样乐器。
我们院儿的大人被人家渗透洗脑了,见自己比不过人家,儿子女儿也眼见得要被人家的孩子比下去,急得火急火燎,逢人就问,逢人就讲,烈火燎原之势宛如肺结核爆发。
我妈叫他们传染了,忙给我请了老师,还天天监视着我练琴,为了防止我“一不小心”碰倒一排码子而无法练琴,唱国歌都不在调儿上的我妈甚至用一套神乎其技的方法记下了哪根弦要拧多紧、码子放在什么位置,从而保证了自助调琴后的音准。
龙兄他妈也被传染了,“病情”恶化之快简直半天就能到纤维化的程度。想他们家那破筒子楼的窄楼道怕是也运不上来钢琴,男孩子也不能学个古筝琵琶的,二胡忒凄凉,小号又太高亢,别的乐器估计也没听说过,他妈就给龙兄请了边上院儿里一个拉小提琴的老头儿教他。
去边上院儿游泳,我也见过那老头儿几次,远远看去那是个很体面的老人。龙兄怕打照面,一看见他就拽着我往浅水区去。我能看见并想起来的,也只有那老头儿的灰白条纹泳帽和他水下不紧不慢的划水了——老头儿那条灰白条纹泳帽戴了至少五年。
龙兄说那老头儿退下来闲得没事儿干,也没有孙子要照看,象征性收学生一点课时费,教人教得仔细极了。
老头儿平常没事儿散步来我们院儿,还时不时到筒子楼边上晃悠,忆苦思甜顺带指点指点学生练琴。只是龙兄总拉不好,一练习曲一小时也顺不下来,时间长了,胳膊脖子一酸,撂下歇会也要挨老头儿批评。老头儿转过来跟他妈说几句,吓得龙兄把老头儿送回南边院儿后不敢回家。
他妈的脾气,大家都知道。

在我的记忆中,有许多个夏天傍晚,我在南边院儿找人下完军棋后,在路边琢磨着前一局的棋路时,碰上龙兄送完老师回家。
夏末的空气湿度大,那院儿又多树,空气黏黏腻腻散发着一股潮霉味儿。我们要走半个多小时,才能走到我们院儿的南门。要松下腿来,真等天晚了,路灯就变得影影绰绰,不时有大蝙蝠或是猫头鹰从高高的白杨上飞走,能吓人一跳。回家再晚了,又得接受家长的批评教育。
可即便如此,我还是和龙兄在那条白杨道上消磨了许多童年时光。龙兄怕回家见他妈,我也不想回家被母亲盯着练琴。
有个伴儿一块儿走,轮流假装崴脚或是抽筋拖延了些时间,每次回家也不是不能交代。不到十岁的孩子,按理说什么也不懂,可总有无尽的话说,攒了一个学期没说完的话,就这样泻在那许多个夏天傍晚。
从大人们兑高锰酸钾拖地到小儿科闹鬼的传说,从学校老师办公桌上的体检报告到开班车的战士的舌苔颜色,我们无话不谈。我们想起一个又一个无厘头的比喻,创造一套又一套能自圆其说的理论,并为此自鸣得意。
我们说世上只有一个大人,不过是化作许多个大人的样子来约束我们,一块儿化成我妈,一块儿化成他妈,还有的大块儿化成胖胖的班主任和教导主任,长相不一样可是一样狰狞,到底大人都是一个人,就像一团儿橡皮泥,这揪一块儿,那揪一块儿,到底也就是原本的一大块儿。
我们还说那幼儿园旁干休所里的老干部,一直在吸收幼儿园里童男童女的“年轻”,因此从不会死,可幼儿园每年也只收院儿里那么十几个子弟,不够他们吸的,所以只能不死,不能变年轻。
而被他们吸没了“年轻”的我们只好离开幼儿园去念小学,换一茬儿比我们更小的小孩儿给他们吸“年轻”。他们一直待在干休所不回家,还天天隔着幼儿园的门对小孩儿笑——肯定是见着了猎物,想着吸来的“年轻”,心里美的。其实他们才是这世界背后的主宰,时间的流逝对他们没有致命的影响,他们一直很老,但他们永远不死,这让我和龙兄都向往极了。我们昔日对那些老干部的崇拜,完全不比今日对虵(此处指某位首长)的少。
当然,话题也并不全是这样不靠谱的童言。比如我们在赶路途中,从对《大×神秘惊奇》里“光绪仍活在现代”这一情节的批评中,确定了彼此对幻想文学的蔑视。《冒险小×队》也因为语言苍白被我们一再吐槽。
我们同样对所有的动物小说抱有鄙夷的态度,打心眼里否定赋予非人生物人格的做法。相对的,龙兄曾用十几个傍晚向我诉说他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崇拜和成为历史学家的决心,我也曾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他自己对数学家这一职业的向往,尽管我与数学家这一职业的唯一交集不过是“某知名数学家生前在我们院儿住过许多年”。
童年的记忆还有普希金、阿城和孙犁,尽管我们谁也没去过白洋淀,更别说是已经不存在的沙俄和文革时的云南了,可这并不能影响我们交换头脑中的诗集与小说,在夏末的蚊虫轰鸣下,一遍遍大声背诵着喜欢的段落,继续我们悠然的赶路。
除去练琴和回家直面他妈的恐惧,我们快活得根本不想走完回家的路,也不想长大。我们那时从不觉得自己会长大,我们永远是孩子,永远与狰狞的大人誓不两立。我们才不可能变成橡皮泥的一部分,我们本身就不屑于变成橡皮泥,更何况我们都是独一无二、无法归一的独立的个体,谁也没能力把我们变成橡皮泥捏一块儿。
其实,我那时心里也不想跟龙兄捏一块儿。我喜欢他的正直,可我也不缺正直。更何况,他的单纯无疑会稀释我的机智。
不过,估计龙兄也有不愿意跟我捏一块儿的理由,他的理由跟我的完全一样也没准儿。话怎么说得来着?——我看龙兄很XX,料龙兄看我应如是。

四五年的夏天就在我和龙兄漫无边际的神侃间过去了。龙兄在那老头的热心指导和他妈的高压政策下有了专业级的水平,我吊儿郎当地竟也混到了业余八级。揉弦时的疼痛已经麻木,指肚也习惯了沤在不透气的白色医用胶布下,但这都不影响我厌恶练琴。
后来,一从学校组织的数学比赛里蒙了个银牌回来,我便借酒撒风向我妈“坦白”自己厌恶弹琴、喜欢算数且有志成为数学家,这得到了她的极大支持——练琴时间从每天两个小时缩减为一个小时。我那坦白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对数学的真爱,而是狡黠孩童对大人的讨好。
我清楚地知道,我妈作为前数学竞赛省队选手,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少女时代的梦想的延续时,必然欣喜。在这欣喜下,如我所料,我妈决定不和我弹琴较劲了,其他小孩儿专业级就专业级吧,能考下来业余八级也差不多行了。说实话,要不是我妈放下了,我和龙兄的革命友谊又要面临一次极其微小的考验。
后来我在班车上跟龙兄玩波波仔,坐我后面的龙兄突然趴到我的椅背上,问我要不要去听听他拉琴。那时我记忆里龙兄拉琴还跟初学时杀猪差不多,没一拍准,没一个音在调儿上,全是琴不想被拉的嘶吼,简直是折磨。
“得亏筒子楼没住老人,要不听你拉琴得心梗。”我开玩笑。
“怎么说话呢?你们楼搭桥儿的,指定是天天听你弹琴崩豆听得。”
隔了半个月,我也没去听,我总觉得我要去了,情景便像是去听胖虎唱歌还要逢迎的小夫了。直到有天晚上礼堂放一部十几年前的经典电影,院儿里没事儿的大人小孩全蜂拥到礼堂去看电影了。
大人们占着后面的好位置,孩子们都被轰到前头,还要大孩子管着小孩子。看见我,龙兄凑过来,有些腼腆地问我要不要去听他拉琴,“现在溜出去,过个十几分钟就回来,大人们不会发现的。”
礼堂里的人乌泱泱的,我又早看过那电影,正想出去喘口气,我就跟着龙兄往筒子楼走。
“欸,你小子是不是就想显摆显摆啊?”路上,我逗他。
“你又听不懂,我跟你显摆什么啊?”他笑我。“我只是学了几年,吃了不少苦,现在拉得不错了,想给哥们儿拉一首听听。”
“‘拉得不错了’,您还说不是显摆啊?”
“不一样,要显摆等不到现在,也没必要跟你面前显摆不是?”他走得不快,却一颠一跳的,是一种极力压抑内心喜悦的步态。
“成,我一会好好听。”
那一路我们一个人也没碰到,连只鸟儿都没看见,简直像是进入了静止的时空隧道。那一路都静极了,树叶子不摆,蝉被热蔫儿了也不叫,我们也没再有更多的对话。传声的介质被抽离,万物都在静静期待着什么似的。
我们走得很慢,都感觉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不差这溜出来的二十分钟。
远处的小破楼一点点大起来,模糊的黑影也渐渐有了层次,那楼上没一点灯光,一块块的黑玻璃像坏了脓的疮,又像要吃了谁似的。眼看筒子楼近了,龙兄却走得更慢了。
“你说长大后我会成为职业的小提琴手么?”他在楼下看着他们家窗台,停下脚步,不愿进楼。
以他当时的水平与年龄来看,成为专业的小提琴手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只是我那时并没明白他的意思,不明白他住筒子楼的自卑与纠结,更糟糕的是,我那时还没有什么对未来的概念,也完全理解不了他的隐秘的热爱。
“先别想长大后的事儿,不去拉琴听了么?”
听我说完,他先是一愣,像是有点失落的样子,旋即又恢复了嘻嘻哈哈的常态。
“筒子楼破,你别进来了,我在窗台上拉给你听!”他跑进楼道,那时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听里面喊,听他噔噔噔跑上楼去。那依旧是四处无比安静的一段时间,以至于我可以听到他在三层小跑过走廊,跑到尽头的水房去,十几秒冲水的声音后那脚步声又回来了,继而一扇窗子被推开,露出一个脑袋来。
他笑得开心极了,俯下一点身子,用弓子指着我喊,“听着啊!”转过身拿了琴,拉起来。
他拉了一首什么什么什么曲,他一说完,我就忘了名字,不过我能感受到他拉琴时的快乐。实际上,除了他的快乐,我什么也听不懂。长长的筒子楼没有一点灯光,他也只是就着薄薄的月光半眯着眼睛拉琴,在溶溶的月夜里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从没见过这样安静而快乐的龙兄。
叫那悠扬的琴声抚摸着,不知为什么我有些不适——大概不是怕他倾着身子从窗台上折下来直接脑瓜儿开瓢儿,是我突然想起他手上的茧了,心像被猛地剐蹭了一下。
那绝非是出于同情或是怜悯,而是突然想起自己也已经感受不到什么揉弦时的疼痛了,惊讶原来我们也都学了四五年琴,和厌恶的乐器磨合了两三千个小时,竟都逐渐麻木、适应了。就像钉马掌,有刺激却没反应了。我们还是成了不嘶鸣、不踢人的温顺的马,任由老师和家长钉上干净漂亮的铁块,而钉上那铁块后,却也能跑得更快更远了,从杀猪崩豆到动人的乐曲,竟也都过来了。
就像童年,竟也都过去了。

去年夏天,我回院儿里取东西,热极了便拐进筒子楼洗了一把脸,叫暗幽幽楼道里的阵阵阴风吹着,确实凉快了不少。我本想着去龙兄家喝碗水,看看他,突然想到他家已经从筒子楼搬走了——他妈得罪过的首长们可算都退了休了。
此刻,龙兄和我都已经成年,成为了一般意义上的狰狞的大人,变成了橡皮泥,和无数的同龄人一起被仓促地捏进了成人世界。
未成年的闸对我们永远地关上,我们很难再溯洄到童年去了——龙兄他家终于搬出了筒子楼,过上了有灶台有马桶的日子;我搬到了离学校更近的陌生社区住,再找不到一起下军棋的人。
我中学上了半年,就断了数学家的念想儿,明白自己这辈子不可能成得了数学家的,证共点又不会证,就是背几个公式,才能维持得了分数这样子;而龙兄,性子还是那么单纯烂漫,只是多了些忧郁,他长大后再也没向我提起过亚历山大大帝,他按照他妈的意愿学了理科,还按照他妈的意愿被物理竞赛搞了,怕是将来要接着按照他妈的意愿接他爸的班儿,再娶一他妈喜欢的媳妇儿。
现在,在一起双排吃鸡远比约着游泳合乎规矩,南边院儿那条要走半个多小时的白杨路现在只要走十几分钟就可以走完,更何况就算是走到尽头,也再没有家长们强迫着练琴了——比起职业乐手,龙兄他妈可能更想让他像他爸一样学造大炮坦克。
龙兄在他妈面前怂了吧唧的,估计没胆儿坦白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但我猜他父母多少能看出来,就是大人们总喜欢装看不出来罢了。我只知道结果:龙兄在上高中前就不学琴了。
我不相信龙兄舍得放下他的琴。
我一直都一厢情愿地相信是那灰白泳帽老头儿得了老年痴呆或是孙子,没法来给龙兄上课了。虽然说“傻笑着逗孙子玩儿”和“傻笑着认不清谁是孙子”,对一个拉小提琴的体面的退休干部来说。都不太体面,但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美好的理由了。
有时候我心里莫名苦闷,待家人睡下了,四处无声了也不能眠。就爬起来,披着月光,也不缠指甲,静悄悄弹一曲自己听。大概因为我从未喜欢过弹琴,也实在怕扰街坊邻居,这样主动弹琴的事儿并没发生过几次,可哪一次弹琴,我都总想着那个近乎真空的夏夜在龙兄家窗台下听他拉小提琴的往事,我总能想起那破筒子楼上的小提琴手。
我总是想着他是怎样噔噔噔跑上楼,从公共卫生间洗了手,回家摸黑打开他的琴盒,怎样走到窗台边推开窗子、俯下身子笑着喊我听好,又是怎样开始拉琴的……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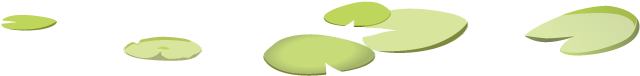
【版权声明】本篇文字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务必注明作者及出处(文学鉴赏与写作,ID:wjjz17),必要时请联系后台授权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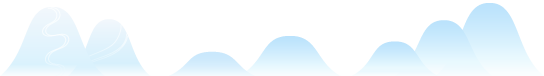
文学鉴赏与写作(ID:wjjz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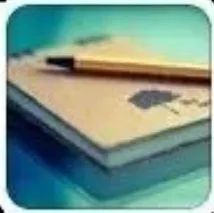
拥抱文学 认识社会 感悟人生

有温度有高度的公益平台,
能让你我在尘世的喧嚣之外,
觅得一份心灵的宁静。
长按上方二维码关注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了解本号及投稿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