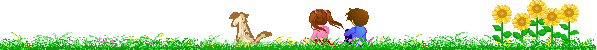“安福文化”旧文整理(十二)
爱故事,似乎是人的天性。孩子们总喜欢在临睡前听会儿故事,才在妈妈怀里安稳地睡去。在这寒冷的冬日,守着这毫无生机的烤火炉,我于是很怀念儿时,一伙人围在通红的灶前火堆旁。老人们点上长长的烟斗,眯上眼睛,将那传说中的故事,随烟头的星星点点、闪闪灭灭,慢慢随烟雾吐出,袅袅飘散,其妙无穷。摇曳的火光映红了孩子们天真的脸,照亮了他们着迷的眼。
儿时的故事中,就有关于老虎的传说。这些故事,基本上都伴随着恐惧。而恐惧留给人的印象总是那么的深刻。多年前读过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的《我的安东尼亚》。大部分内容都已经忘记了,而独独有一个情节,记忆犹新,想来也是因为恐惧。书中讲了一个发生在俄罗斯的悲惨故事。在一个没有月亮只有星光的冬日的晚上,成群的饿狼如何吞噬了几乎整个欢乐的迎亲队伍,只剩下最后一辆跑在最前面的雪橇。车夫把新娘和新郎推下了雪橇,留给了狼群,独自奔向那村子里修道院传来的、召唤早祷的钟声。我的记忆里,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我的家在安福北山脚下。老人们常说,村里以前正月耍龙灯,一行人敲锣打鼓直耍到北山山口去。每一年这一行人中,走在最后的便入了虎口,再也回不来。
这两个故事,遭遇相似结局却截然不同。薇拉小说里的故事结尾很现实很凄惨,两个俄罗斯车夫遭到村里人唾骂,被赶出了村庄,流亡到美国,终老难安。而现实中的传说却反倒浪漫而神奇。
老人们说,老虎吃人许是虎精作乱。于是请来神仙帮忙。结果神仙道破玄机,村子是个虎形。村中的两口古井是老虎的眼睛,老虎的肚子在村北的某处。神仙指点村民准备两大箩筐绣花针,倒入古井。据说井里翻腾了几天的通红的井水,那是老虎眼睛流出来的血水。算是刺瞎了老虎的眼睛。村民们又在神仙的指点下,在老虎肚子处挖了一口池塘,将老虎开了膛剖了腹。相比爷爷说的老虎跳进猪栏里把猪叼走,将尾巴伸进狗洞把狗卷走那些真实的事情。我更喜欢琢磨上面这则传说,并试着解读。正如传统文化学者朱东在《破解传说的密码》中所说的——
“当我们面对这些传说的时候,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种故事来听,而是要将其中的所谓夸张与比喻,视为一种表达方法,表现手法,来透过种种神奇,看到一些历史真实的影像。或者说,那些夸张和比喻,往往就是我们破解这些传说的密码。”
我想,隐含在这则故事后面的叙事至少包含了以下几个内容。首先,是村民们对老虎的真实的恐惧。武功山及周边地区自古多豺狼虎豹,胡朴安在其《中华全国风俗志》中“安福民风琐记”篇就有“虎狼野兽,时有所猎,有扛至市中求售者,虎皮一床,索价七八元”的记述。村后就是高山密林,虎患猖獗。80年代晚上还能听到老虎的叫声,村民晚上早早关门。我自己也见过一只小老虎,因为太小,只觉得像猫。经年累月,他们心里对虎患的恐惧便不自觉地进入了灶前火堆边漫漫长夜的故事中,还有不耐烦的妈妈对不愿入睡的孩子“老虎来啦”的恐吓中。另外,这也是人类与兽类争夺生存空间的博弈。故事中形象巧妙地利用了谐音“睛”来喻指井,用“膛”来喻指“塘”。用“塞睛开膛”来比喻填井挖塘这样的早期村民的经济开发活动。将之和虎患联系起来,是如黄志繁所说,“以往的研究已经揭示出,虎患是人类的经济开发活动破坏了老虎居住的生态环境所致”。马立博(Robert Marks)更把老虎活动看成人类入侵和破坏自然环境的晴雨表。
关于历史上武功山及周边地区的老虎,萍乡胡可南先生的文章《武功山拿老虎说事》史实颇丰,见地也深。胡先生没有把萍乡明代知县陆世勣慷慨豪迈、为民除害的叙事诗《武功山射虎行》囊入文中,而选择了南朝安福人王孚的《安成记》中义虎报恩和《后汉书》中安成长刘陵因修德政而虎出界几则故事。想来不是因为《射虎行》“牧子充熊肠,樵夫挂虎齿。田畴遍蒿莱,场圃皆荆枳。遗钹纷纵横,暴骸怜填委。为民父母心,伤哉痛欲死”这样的诗句不够给人震撼、打动人心,而是作者心中自有丘壑。所谓“夫虎豹在山,鼋鼍在水,各有所托。且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今为人害,咎在残吏,而劳勤张捕,非忧恤植稻也。其务退奸贪,思进忠善。”武功虎故事,或“谈虎色变”,或“与虎共舞”,都是历史一定程度的真实。静静听来,慢慢读来,总能在这“虚幻的世界”里触摸到几分真实。
古庐陵甚至还有一则苏易为虎接生的故事,搜来以飨读者:《搜神记》曰:苏易者,庐陵妇人,善看产。夜忽为虎所取,行量蕊至大旷,见有牝虎当产,不得解,匍匐欲死,辄仰视。易悟之,乃为探出之,有三子。生毕,虎负易送还,并送野肉於门内。 奇哉,善哉。
2015年1月18日

野莲小语,对话生命

长按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