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访者:王淑娟,内蒙古巴彦淖尔人,法学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先后获得国际政治学士学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博士学位,曾在日本东北大学、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访学。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研究。
采访者:马语晨 清华大学哲学系硕士生
《法哲学原理》读书会五周年系列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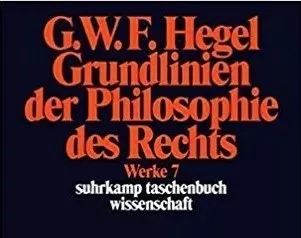
Q1
为什么会被读书会所吸引?多年以来坚持参与读书会又是出于何种缘由?从当初到今时,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读书会时的心境是否发生过变化?

Q1
我是2011年开始参加韩立新老师主持的读书会的。当时我的导师刘敬东老师要求我一定要去上几门课,其中之一就是韩老师的读书会。从那时开始到今天已经7年有余。其实读书会经历了很多个阶段,2011年的时候韩老师正带着大家读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法哲学原理》是最近的一个阶段。
读本科的时候我是学国际政治的,后来改学哲学。虽然学科有变化,但是读书做研究的方法却是一致的。学国际政治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讲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也鼓励我们课下去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的原著《国家间政治》,我自己也读过一本摩根索的学术传记。虽然我已经不再专门从事这个学科的学习和研究,但是用原著磨出来的思想印记,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历久弥新。那时我开始明白读原著的重要性。进入韩老师主持的读书会,发现会上也是这个做法。对于这种方式,我倒没有太多不适应,但是碰到读一段文本读一整天丝毫读不出其中深意的时候,也不免会觉得灰心。不过,我渐渐体会到这是做学问应该走的道路,没有其他的捷径可寻。
哲学是一个久远而又新鲜的学科。久远是说这门学科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常常由来已久,哲学史上无数的思想家都试图回答类似的问题;新鲜是说这些问题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每个时代的思想者总能提出新的洞见。比如政治哲学免不了要讨论这么许多的个体究竟如何能够或者应该如何共同生活在一起。这就像是一场长久的论战,每个思想家生活的时空虽然不同,却都是这场长久论战的参与者。武林高手在前面过招,棋逢对手,正是热闹。读二手文献,就像是听挤到前面的人转述个中高手的功夫如此这般精妙,但总是隔岸观火,将信将疑。总得自己挤到前面,亲眼看看才能知道是不是果然如此。甚至有的时候自己心里也痒痒的,想到论战中一试身手,不论功夫高低,总要试炼一番。这种身临其境的乐趣,穿越时空阻隔、触及历史上思想家们留下的文字,与他们直接对话的感受,只有直接读原著才能体会得到。当然上面这只是个浅陋的比喻,为了说明我自己在读原著中所体会到的快乐;但是政治哲学本身涉及千万人的现实生活,甚至生死存亡,本不该用这种戏谑的语言来描绘。
Q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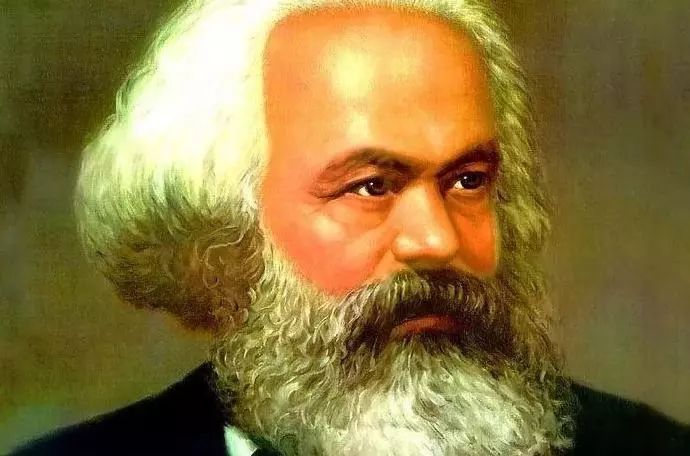
您在参与读书会之后,采取何种方式切入文本的问题意识与具体意涵之中?您认为读书会对于您的学术生涯而言具有何种意义?
Q2
细致的研读原著,无论是马克思的原著还是黑格尔的原著都会涉及到很多背景知识。对于著者自己和与他们同时代的读者来说可能是常识,但对于我们来说却导致了很多理解上的困难,甚至是误读。记得为了读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穆勒评注》一节,我先去读了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要义》。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老穆勒甚至是一位早就被扔进故纸堆里的人物,但是要读《穆勒评注》,就不得不把老穆勒先生请出来,好好地先向他讨教一番。我这才发现老穆勒先生虽然比小穆勒(即约翰·密尔)和马克思年纪大,也远不如后面两位出名,倒也不总是“庸俗”,《政治经济学要义》自有其中的道理。当然要读《巴黎手稿》,还需要把许多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请出来,有些是马克思的前辈,有些是马克思的同时代人,不然我们就无从知道马克思究竟在与这些人争论些什么,哪些观点是他们的共识,哪些观点是马克思独树一帜的洞见。或者更一般地说,要理解马克思、黑格尔这样一些思想家的著作,可能不得不深究文本当中每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词句,穷根究底,才能逐渐拼接出历史的、哲学史的或者他们个人思想变迁史的总体图景,在一个立体的坐标系中定位和理解某一文本的独特意义。
我曾经读过马克斯·韦伯的《以学术为志业》。韦伯在其中讲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祛魅的现代社会,很难有一种宗教或者一种信念能够统率人心。教师不再是神圣教义的代言人,不再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而只是某个专业领域中的工作者。一个教师在课堂上阐述某种思想,他不仅要告诉学生们这个专业或者这种思想的解释能力,也要告诉他们这个专业或者这种思想的解释限度。至于说学生们对哪一种思想心悦诚服、欣然笑纳,那是他们自己的理性选择,不能由教师直接替他们决定。在《法哲学原理》等一系列的读书会上,老师们同学们就是如此。韩立新老师、陈浩老师还有很多的老师们虽然承担着引领、督促的工作,却不是一言堂,总是鼓励大家发表自己的观点,最好是批判性的观点。这个读书会教会我反思、批判的方法,更激发了我敢于说出不同意见的勇气。
如今我也开始承担教学工作,走上了讲台。不管具体的教学任务有什么变化,至少在读书会上建立起来的两个信念是始终不渝的。第一,老师自己不读书,没有资格上讲台;第二,老师和学生的差异不过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二者是地位平等的理性个体,只有在共同的批判和反思中才能有真知灼见。
Q3
读书会自开办至今已逾五年,您作为最早的一批参与者和见证者,在读书会的主题设置、研读方式与互动形式等方面有何意见与建议吗?您作为读书会的前辈,对这批新加入的后学者有什么寄望与嘱托吗?

Q3
对于读书会唯一的建议是希望能够适当控制讨论的进度,遇到意见不统一的情况,只要大家都已经充分表达和理解了各自的观点,就不必继续反复停留于此,可以继续推进。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本身就是一个体系,在继续推进的过程中,以往讨论过的问题并不会丢失,反而总会遇到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继续引向深入的新契机。
对于读书,特别是读哲学来说,我们所碰到的可能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是说,在民族危亡的时代,国土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所以前辈学人们学工程学技术,学马上能救国救民于水火的知识。我们生在和平发展的时代,可以在平静的书桌前坐下来,不为衣食住行发愁,学一点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其重要意义需要较长的时段才能体现出来的学科。最坏的时代是说,这是一个市场化的时代,甚至学术研究有时也不得不按照市场机制来运作。面对市场提供的各种压力和各样诱惑,能不能在书桌旁坐下来,心无旁骛,不急不躁,花几年的时间读一本经典,这实在是一种考验。不论是前辈还是后辈,希望我们都能经受住考验。
— END —
文本中的时代和新MEGA研究
?长按二维码关注: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
